男子异乡当窑奴112天 每天劳动约17小时

每次回想起在云南的那段非人生活,徐兵都感到心有余悸。
据重庆晚报8月24日消息,昨日,重庆江北区的汉子徐兵,从云南省宜良县检察院获得消息:用暴力手段强迫他和几十个民工劳动的砖窑老板高某某等3人已被追刑,徐兵可在当地法院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
至此,一个几乎一样的噩梦已折磨他大半年———他身穿难辨颜色的衣裤,和同样肮脏的一群男人挤在黑屋大通铺睡觉;每天劳动约17小时,稍有怨言就被皮鞭抽背……最近一周,徐兵总在噩梦中醒来,满头冷汗,剧烈心跳让他屏住呼吸都能听见。
“现在,我要是不把我的遭遇讲出来,心里堵得慌。”昨日,徐兵鼓足勇气详细讲述了那段长达112天、曾被左邻右舍认为“觉得像吹牛”的窑奴经历。
第1天
拖上车拉进黑砖窑
不愿打工遭皮鞭抽
我叫徐兵,今年36岁,住江北区铁山坪街道马鞍山村内沱组160号。爸妈死得早,我是孤儿,堂哥徐明是我最亲的人。这几年,我靠四处打零工谋生。
去年7月初,听人说去云南打工好挣钱,我找堂哥借路费出发了。谁知,好工作没找到,霉运却来了。记得那天是7月25日下午5点左右,我在昆明市石林县的公路边走,钱差不多用完,我想节约车费买点吃的继续找工作。
突然,一辆面包车一个急刹停在公路边,跑来3个30岁左右的男人。
我遭吓了一跳,站在路边不敢动。两个人一左一右把我按地上,等我抬头的时候面包车开过来了。他们不说话,拖我上车。我以为遇到抢劫,扯起喉咙喊救命。有个高个子扑过来,使劲卡我脖子;剩下两个对我脑壳和背乱打。
他们打了我五六分钟,见我不再反抗就拖上车。隔着车窗,我看见沿途很偏僻。
司机是个接近30岁的男人。后来,我才晓得他是黑砖窑的小老板,好像姓高。
大概1小时左右,面包车开进公路边一座砖窑。我看到有近30个、二十多岁至五六十岁的男人在灯光下做砖坯,有人提皮鞭监视。
砖厂大门那里,有两个提铁棒的人跟拖我上车的人打招呼。他们讲当地话,我听不懂。
他们把我拖进一间平房,问我愿不愿意打工。我问工资好多,司机嘿嘿笑了几声。我以为他没听懂,又问。这时候,一个在外面监视干活的人进来。他提皮鞭抽我,我捂头蹲在地上,鞭子落在背上,痛得钻心。
我想,跑不可能,要工钱更是做梦。没办法,我答应留下来干活。
当天晚上,我被安排到一间与另一间平房相连的10多平方米的房子。屋内没门窗,只有七八米长的大通铺,被子脏得辨不出颜色。
两间屋的工人有二十八九个,进出都有4个监工男人把守。
第2天
每顿吃白菜吞干饭
干17个小时不休息
晚上,做砖的人陆续回屋。我听到有个五六十岁的老头说重庆话,就靠过去问他是重庆哪里的。他刚讲“合川”两个字,就双手抱头蹲地上———监工抡起皮鞭打过来,他背上立即冒起一条指头粗的红印子。
再不敢说话,好不容易挨到天快亮。平房外传来吆喝吃饭的声音。没有人敢贪睡,像弹簧一样从床上爬起,往屋外坝子小跑。早饭是看不到油花的炒白菜,干饭每人只准舀一碗。
吃饭时,头天晚上抡皮鞭打我的那个人给我讲规矩:不准跟其他人讲话,不然挨打,再不听招呼就得从砖窑“消失”;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吃饭,5点半干活,中午12点吃饭,12点半继续干活,晚上6点吃饭,6点半干活到晚上11点回平房睡觉;隔10天吃顿肥肉炒菜,平时每顿只能吃一个素菜和一碗干饭。
白天和晚上,我上了两次厕所,解的都是小便。后来,我才发现,在这里做砖坯的工人,几乎每隔两三天才解次大便———吃不饱饭,解大手的间隔时间被延长。
每次上厕所,都有一个提皮鞭的监工跟踪我,有些人上厕所却不被跟踪。后来,我悄悄问同伴原因,他们讲,关在这里时间长、监工认为彻底被打服再不敢逃跑的人,上厕所时才不会被跟踪。
晚上12点钟左右,有个20多岁的贵州人在监工跟踪下上厕所。没几分钟,其他监工提铁棒或钢管跑出平房。很快,屋外传来呻吟声。又过几分钟,监工押贵州人进屋,一下把他丢在通铺上,给我们讲“他就是逃跑的下场”。
贵州人脑袋不断冒血,整个晚上都没动。第二天,他被监工抬起甩进面包车,不晓得拉到哪里去了。
那里的天气早晚凉,中午和下午热得让人受不了。一些在这里做砖坯时间长的人,受每天跟冰冷泥巴打交道影响,冬天被冻成冻疮的裂口仍无法愈合,砖坯上常沾着丝丝血迹。
·凡注明来源为“海口网”的所有文字、图片、音视频、美术设计等作品,版权均属海口网所有。未经本网书面授权,不得进行一切形式的下载、转载或建立镜像。
·凡注明为其它来源的信息,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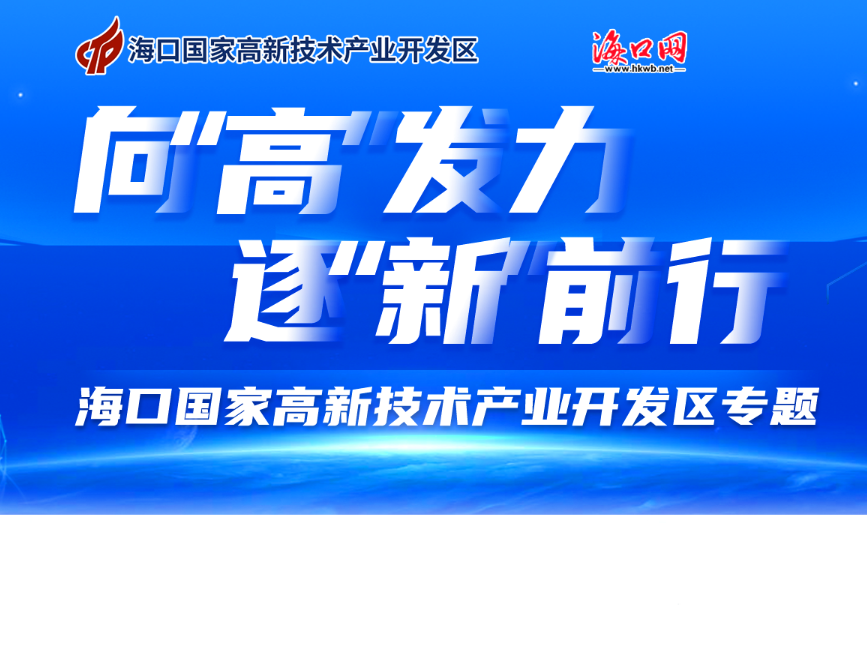





edef585a-fede-4ca8-bfa9-10e036755de3_zsize_watermark.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