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人体器官捐献移植链条(图)

躺在手术台上的钟腾瑜。

2012年4月1日,广州市南方医院急救中心,身患绝症的90后男孩儿江立权决定自愿捐献器官。

医生们向钟腾瑜默哀。
6月9日,佛山市一医院。
手术室里穿梭着不同的医生,有心脏科的,有肾病科的,有肝脏科的,还有从广州赶来的眼科医生。他们,都围绕着躺在手术台上的一个患者。
躺在手术台上的人叫钟腾瑜,45岁,广西融安人。6天前,45岁的他突发脑溢血而脑死亡,就再也没能醒来。
隔壁手术室,还躺着4个病人,4个被病魔困扰即将离世的人。
片刻的默哀后,钟腾瑜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心脏、肝脏、两个肾,将分别移植到隔壁手术室的4个病人身上。
这天,死亡对于钟腾瑜来说,是“凤凰涅槃”般的蜕变。
捐献者的考量
叫声“妈”很难吗?
其实,钟腾瑜并不认识这4名需移植器官的患者,他的家人也不认识。尽管钟家人想知道捐献的器官救了谁,但却不能知道。
钟腾瑜脑溢血入院的第三天,就没有了自主呼吸,处于脑死亡状态。
器官捐赠协调员彭宣祥从禅城区中心医院得知消息后,随即见到了钟腾瑜的家人,在“捐献器官是为了延续别人生命”的倡导下,钟家人同意捐献。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签字办手续,并陪着钟腾瑜走完最后一程。
当钟腾瑜获得“生命延续”时,深圳龙岗中心医院病房的罗某正在生死线上挣扎。
一个星期前,罗某因感情问题绝食自杀,当房东发现时他已奄奄一息,仅靠呼吸机维持最后的生命。从河北老家赶来的父亲纠结了:一边是毫无希望的救治,一边是每天不少于3000多元的医疗费。当他见到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后,决定将儿子器官捐献,因为一旦捐献成功,余下的医疗费就不用自家承担了。
与罗某父亲不同,广东清远一位老人有着自己的考虑。不久前,老人22岁的女儿因车祸脑死亡,老人愿意捐献女儿的心脏救人,但有个要求,希望受益者必须是女孩,还要见上受益者一面,让受益者也叫她“妈妈”。无论怎样解释,老人始终理解不了:“我女儿的心脏都给了她,难道我们见见都不行吗?”
彭宣祥说,他有四种人不接受捐献器官。一是植物人,二是活体,三是死刑犯,四是三无人员。
高敏担心,“请把我的肾还给我”的一幕会在中国发生。
真实故事的隐喻
“请把肾还给我”
“请把我的肾还给我”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据高敏介绍,国外一个男人捐肾救了一个女人的性命,两人相爱结婚。后来感情破裂,两人闹离婚至法庭。男人什么要求也没有提,只要求“请把我的肾还给我”。
“现在的无偿捐献和坦诚,并不代表永远。”高敏说,器官捐献者的家属一旦知道受益者是谁,不能保证将来会发生什么,到那时,两者如何面对?
真的会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之一,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任该医院院长。此前深圳11岁的小孩田干器官捐献救了5人,就是在这家医院移植完成的。
在该医院移植中心,46岁的秦某躺在病床上安养。他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等了两个多月才换上肝,在医院养身体等待期间就花了10多万元,而移植的肝花费了15万元。“我不知道肝是谁的,感激是肯定的,但并不想知道是谁的,无论怎样说,移植肝我花了不少钱,我付出了。”
另一位接受肾移植的患者刘某也如此认为。他说,“肾移植花了10多万了,医生只告诉我肾是一个20多岁年轻人的,别的都没有了。”
华西都市报记者随机调查的15名患者中,仅有一人愿见捐献者家属。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不愿见捐献者,并非是自己没有良知,而是自己花费了不菲的医疗费,怕见了捐献者家属,会遭遇过分要求。
协调员的角色
“医院与捐献者之间的润滑剂”
彭宣祥并不是医生,也不是家属,而是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佛山工作站的协调员,一名红十字会编外成员。他的出现,只不过是适应器官捐献必须委托第三方机构中国红十字会来负责捐献组织工作。
广东目前有5位专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广州2人,深圳2人,再加上他。在全国,也仅有91位专职协调员。
44岁的彭宣祥,是湖北汉川人,原本只是深圳一位普通的农民工。至今,他称已劝导29人成功捐献器官,其中仅一人是深圳人。
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
室协调员高敏情况也差不多。
45岁的高敏是济南人,来深圳快20年了。她自称献血200多次了,如今是全国女性献血最多的人。她也说,自己已有40例成功的器官捐献案例了,眼角膜的捐献达到了300多例。
第一次的成功不仅难忘,也最为触动她。2005年,高敏接到湖北天门的一个求救电话,王大姐的女儿遇车祸脑死亡,想捐献器官,问了很多红十字会均未成功,后来找到高敏,圆了这个心愿。
而专职协调员最早出现在2007年,那时被称为劝捐员。高敏觉得“劝捐”不好,“协调”就不一样了,将捐献者放在了首位,至少是一种尊重。
高敏认为,协调员的工作应该将心比心,理解每位捐献者。“我只是一个铺路的石子,是医院患者与器官捐献者之间的润滑剂而已。”
事实上,并非每位器官捐献者都能捐献成功,“润滑剂”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31岁的庞泉是深圳的公交司机,因脑瘤住进了医院,去年4月签订器官捐献书,2个多月后心脏停止跳动,欠下医疗费13万多元。尽管捐献没有成功,高敏还是通过自己的“名人效应”,找了多家机构,总算在11月份交齐了费用,“对家属总要有个交代吧。”
高敏说,红十字会只是每月报销车费、电话费等,就没有别的收入了。
彭宣祥也说,最痛苦的事,是家属签字拔停呼吸机时,那一刻,死亡和新生交融。每每经历这种生死,都是一种煎熬,他常常说服自己,这只是一份工作。
被逼进死胡同
“给了钱就是买卖”
捐献器官救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生命的逝去,一个家庭的破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埔院区ICU主任杨春华,是一位器官捐献评估专家,该医院每例捐献者都要经过他的评估。
杨春华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根据相关规定,器官捐献必须在死亡后进行,在医学上最基本的判定是脑死亡,经过家属签字放弃后,才可停了呼吸机,也就是心脏停止跳动,才可以从捐献者遗体中摘取器官。
他说,一般5个脑死亡患者中,能有一个器官捐献成功就算不错了。脑溢血、车祸的脑死亡者,是目前最好的器官捐献者。他经手的30例评估中,成功的有20多例,“这在国内也算是高的了”。
“坦白而言,器官捐献者中,打工
的外地人所占比重最大。”
现实中,“禁止买卖器官”的限定,在遇上器官捐献后,存有一些操作难题。“很多捐献者希望得到经济上的补偿,这本身与无偿器官捐献的主旨相违背。”杨春华说。
去年,湖南的一位捐献者同意无偿捐献,可等医生赶到湖南取器官时,家属突然不干了,要一笔钱,红十字会和医院得知后只好放弃,“给了钱,就是买卖器官了”。
杨春华告诉记者,一般原则下,对器官捐献者的家属,医院会在经济上给予一定补偿,更多是帮忙解决部分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此外,红十字会也会倡导社会捐款,为家属开设专门账户。“卫生部和红十字会并没有专门的经费,用于补偿器官捐献者的家属。”
一边是因家境困难,而希望得到经济补偿的器官捐献方,一边是负担高额医疗费,而不愿见捐献者的受益者,两者之间似乎难于调和。
这样,充当中间者的协调员就会显得举步维艰。
“在深圳,对家属的补偿一般不会超过两万元。”彭宣祥说,他现在的做法是,一旦经过接受器官医院的评估后,捐献者余下的医疗费就由该医院承担,还包括丧葬费等。
佛山市一医院副院长章成国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这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为了鼓励器官捐献。”他们医院去年7月份才拿到批复文件,允许医院开展器官移植,此前的2006年被叫停,“供体少是目前最大的困境。”
章成国称,他们也在探索器官移
植的发展方向,而通过经济补偿来刺激器官的捐献,将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根据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讲话,我们总结了四条原则,一是公民自愿捐献,二是以心脏死亡作为死亡标准,三是红十字会负责器官捐献,四是采取经济补偿与激励政策。”
更有甚者,常有人给高敏打电话要求捐肾,有的是缺钱了,有的是不想活了……每每这时,高敏总是耐心开导,急了就说“跳楼、喝农药自杀的,器官想捐也捐不成”,这时电话那头就感叹了,“想死都这么难,那算了,我不死了!”
这些年来,高敏最难忘的是一张国外宣传照片一个小女孩趴在一位老人胸口上,“听着父亲的心跳”。她希望自己也能亲眼见到这一幕。
·凡注明来源为“海口网”的所有文字、图片、音视频、美术设计等作品,版权均属海口网所有。未经本网书面授权,不得进行一切形式的下载、转载或建立镜像。
·凡注明为其它来源的信息,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1fb5b768-69f0-4423-accf-30cf422eefb6.jpg)
50be6c67-2eb0-451d-b539-8920c063dabc.jpg)
e9737f04-eb51-4eb2-8289-f372798466c0.jpg)
ebb19d47-d6b5-4b61-9b53-b10a8305b5fa.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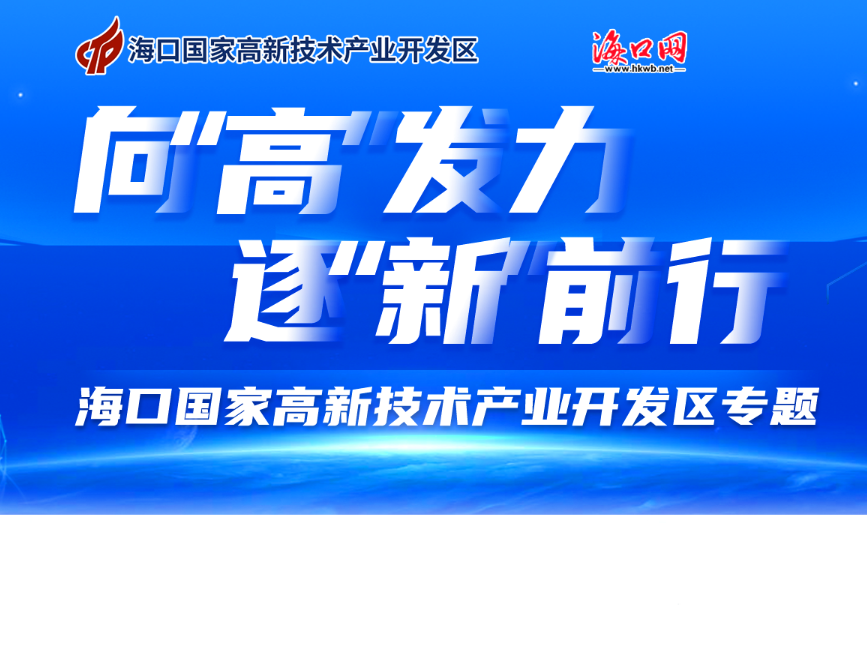





edef585a-fede-4ca8-bfa9-10e036755de3_zsize_watermark.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