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万山矿工陷汞毒泥潭 "汞都"申请20亿元治毒
工人们知道汞是有毒的,但是靠山吃山,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习惯了,免疫了,也只能靠这活来增加收入,要不没钱花。
大龙镇重谭组的刘婆婆说,被污染的田种出来的米是“黑”的,大家都不敢用来吃,只有多洗洗然后煮来喂猪,大家都是买米吃。
非法土方蒸气练汞作坊下美丽的村落,显得很宁静.
吸毒的失意群体
申玉珍的步履,像一位负债累累的母亲在愁苦地跋涉。
她和黄亚平同住万山同心社区B区。这位71岁的老妇,走路有些瘸。她的腿是在2008年开始瘸的。那年,她去贵州省委上访,在省委门前的地上睡了一个礼拜后,腿就开始瘸了。此外,她还有高血压和脑萎缩。
申玉珍是矿工家属。1998年,她的丈夫在贵州汞矿工作了35年后,因矽肺病晚期去世。1993年,小儿子姚本强,被贵州水钢招去做电焊工。大儿子姚本发,一直在贵州汞矿做冶炼工。弟弟去贵州水钢这年,姚本发结婚了,妻子吴氏是万山人。
2001年,36岁的姚本发工作8年后,贵州汞矿关闭,他拿到1.9万元买断工龄安置费。第二年,失意落魄的姚开始吸食海洛因。刚开始,1克海洛因50元,后来涨到100多元。
1.9万元很快就被花光。他后来成为低保户,每月有230元低保金。
钱花光后,他卖掉万山三角岩家里结婚时买的彩电、沙发、戒指和床铺。家里值钱的物什全都变成他的毒资。毒瘾鬼魅般如影随形。他开始和其他吸毒的人一样,四处寻找废铁卖。
三角岩是贵州汞矿工人的一个聚居地。除了当年的行政中心土坪外,三角岩是所有贵州汞矿10个工人聚居地中的第二大社区,人口最多时有1829人。
汞矿关闭后,待业青年们喜欢在这些社区里晃荡。后来,海洛因也开始进入这个社区,成了部分无业和失意工人们释放烦恼的东西。有时,贵阳有也有零包贩毒人员来这里兜售海洛因。
姚本发也是这个失意群体中的一员。
没有钱买海洛因时,姚本发痛苦得在地上打滚。看到儿子的痛苦状态,申玉珍偶尔也会从微薄的抚恤金里,拿出一点给儿子买海洛因。姚本发曾在戒掉毒瘾后,在万山找过工作,但对方说他吸过毒,名声不好,不愿聘他。
有一年,申玉珍给了1500元,让儿子去外省找工作。10多天后,姚本发回来了。母亲给他的钱也全部花光。他说自己去过湖南、浙江和广东等地,工厂招工的人都说他年纪太大,不愿录用他。
2004年,妻子吴氏跟他离婚了。
他继续开始吸毒。2013年12月6日,他被当地抓去万山戒毒所强制戒毒。
当毒瘾越来越大时,有的吸毒者开始选择注射吸食海洛因。万山一位公务员说,曾有人因为过量注射而死亡,被人们发现时,尸体已开始腐烂。
7月2日上午,万山阵雨。三角岩一派静谧。这个四处房屋垮塌、灰蒙蒙的小区里,空寂冷清。如果不是偶尔从一幢平房里传出来的电视节目声音,以及偶或突突驶过的三轮出租车,会让人有步入一座死城的错觉。
随意推开一间房门,潮湿和发霉的气息扑面而来。现在继续留在这些破败房子里的,是少部分60-70岁的老人。无论白昼黑夜,他们都不敢离开屋子太远,因为经常有一些吸毒的年轻人,趁他们不在家时,溜进屋里盗窃一切值钱的东西。几幢上世纪80年代前后修建的楼房里,铁制窗棂也大多被偷走。
申玉珍说,当年为了帮国家还苏联的债务,贵州汞矿做了数亿元的贡献。“凭什么现在让我们来承受这样的生活?”
鞋穿重了就走不动的汞中毒者
黄亚平的红色三轮出租车,如果穿过同心社区,再通过汞都大道、汞都路、辰砂路,几经蜿蜒后,就能在5、6分钟后到达3公里外的土坪路。袁仁纯家就在这条路上一幢破旧的单元楼。
袁仁纯在吃午饭,酒杯里的酒快要喝完了。
10多分钟后,这位72岁的老人再次端着杯子,手指颤抖着喝光最后一口酒。
1965年,他开始在汞矿工作。1989年9月,他被查出汞中毒,鉴定为8级工伤。后来,他被送去贵州汞矿技校附近的疗养院疗养。疗养期间,每天伙食不错,但根本吃不下东西。
自周秦以来,中国就开始用丹砂来炼制据说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丹药。现在,这种被命名为汞的致命元素,正让原贵州汞矿部分职工,承受着中毒后的痛苦。
袁仁纯说,汞中毒后,走上坡路时双脚乏力,经常性头晕。
当年,贵州汞矿红火时,袁仁纯曾在五坑做过冶炼的大班班长。那时每月要生产8吨汞,生产压力和工作强度都较大,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与汞接触的频率很高。
据《贵州汞矿史料》记载,在官方正式接管贵州汞矿两年后的1954年,就曾因134人次汞中毒,而导致休工达600多日。之前,贵州汞矿的冶炼一直采用土灶,回收率仅为50-60%,“这意味着有40-50%的汞呈蒸汽逸入空气中,汞蒸气浓度超过标准460倍。
那时,在汞矿工作时,袁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颇受敬重,“现在没人管我们了。”
另一位汞中毒者刘黑子,两年前已去世。
2011年,澎湃新闻采访他时,这位79岁的矿工,住在万山冒水垄路一幢80年代修建的单元楼1楼里。他左手端着饭碗,右手握着筷子,正艰难地往嘴里扒饭粒,一双手不停地颤抖。导致他双手颤抖的,正是多年从事汞矿工作所带来的汞中毒。
在他20多岁时,他的汞中毒症状,仅是口腔溃烂。
刘黑子55岁的女儿刘绍萍拿出一个白色药瓶,上面印着“丙戊酸钠缓释片”字样。女儿回忆,父亲早晚吃一片,以此来缓解双手颤抖。除了双手颤抖外,他还是一名尘肺病二期患者。
在刘黑子的记忆中,他6岁开始接触汞。那年,他和母亲从家乡湖南麻阳县一路乞讨至贵州,最后在贵州汞矿做了一名童工。在矿上,和他年龄相仿的童工有很多。他没有想到,这一生的命运轮盘,从此与地球上唯一的液态金属挂上了钩。
不断颤抖的手脚,让刘黑子的行动有些迟缓。他用手摩挲脸颊时,手是颤抖的,无法控制,“内心很慌”。走路不能穿厚重的鞋子,“每天都只能给他穿轻便的鞋子,重了就走不动。”
刘黑子仍记得,他的汞中毒是发生在1960年和1961年。那时,他所在的贵州汞矿五坑,每月要生产30吨水银,只有他一个人装罐,每罐装50斤。
后来,矿上要求矿工中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在矿洞的逼仄空间里,用高压水冲洗汞矿石,并用刷子将含水银的部分刷下来,再用木炭炒。年轻的刘黑子是党员之一,他因此而成为洗矿工人。一洗就是好几年。他的开始口腔溃烂,直到他感觉“不对”,才换了其它岗位。
1963年7月25日,贵州汞矿在对矿工做体检时发现,矿工中汞中毒者有151人,患病率为6.6%。刘黑子正是这6.6%中的一名。24年后的1987年6月底,这个数字增加至274人。这是贵州汞矿关闭前,最后一次出现在《贵州汞矿史料》之“贵州汞矿大事记”里的记录。
在万山的“双转型”中,这批汞中毒者,仍在继续承受着手脚颤抖、易怒、烦躁和精神错乱等带来的痛苦和烦恼。他们中的部分人,有的只吃一些维生素,有的根本不吃药,“让汞自己慢慢排放出体外。”
·凡注明来源为“海口网”的所有文字、图片、音视频、美术设计等作品,版权均属海口网所有。未经本网书面授权,不得进行一切形式的下载、转载或建立镜像。
·凡注明为其它来源的信息,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d29b69aa-982c-4a91-886c-32ef20dbcedc_zsize.jpg)
1d68e0a1-0d60-4404-8c9d-4a5b44231d20.jpg)
9a662db5-7b63-433f-99d0-2fdef316a32e.jpg)
a65a8618-af8e-4e04-8bd6-828d946b67f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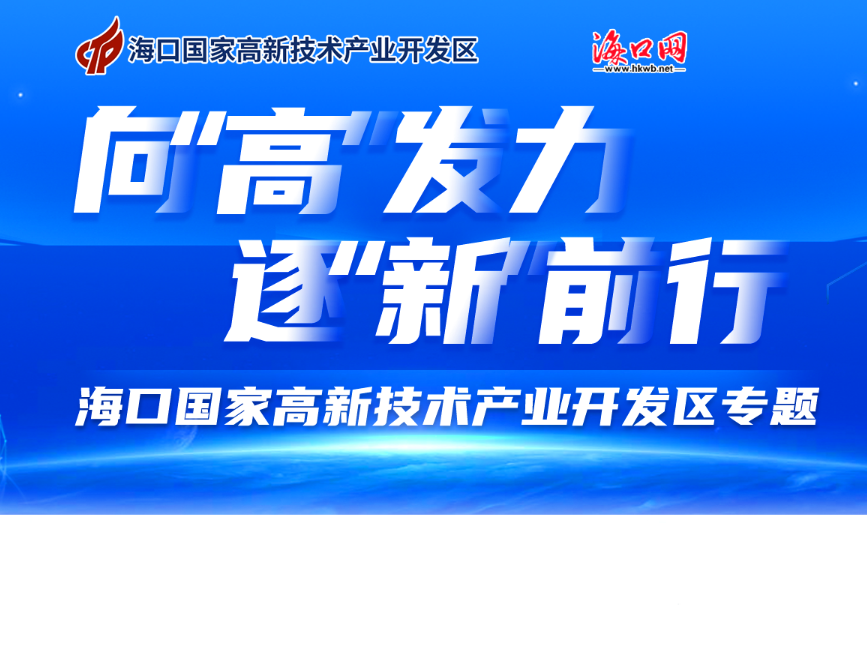
97b1ac89-f234-4738-8c73-6eb2057278e9.jpg)


bc6ffb65-1884-4ceb-be9f-80cb234baf33.jpg)
7c094eee-77ee-447e-949e-cd3d56eaabf8.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