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名与相知(新书创作谈)

《棔柿楼集》:扬之水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名物学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先秦时代即已产生,此后依附于经学而绵延不绝,直到近世考古学的兴起才逐渐式微,乃至被人们淡忘。重新拾起这一名称,是因为人们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中发现,这一方法可以为传统的名物学灌注新的生命。而在考古学逐步走向成熟的今天,我们完全有条件使名物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解决文学、历史、考古等领域中遇到的问题。
“名物”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周礼》所做的工作便是用器物和器物名称的意义构建礼制之网,它因此为后世的名物研究奠定了基础,确立了基本概念。宋代的金石学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以当代情怀追溯、复原乃至编织远古历史。
而当今之“名物新证”的概念,则是由沈从文先生率先提出。在《“(分瓜)瓟斝”和“点犀(上喬下皿)”》一文中,他解释了《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节中两件古器的名称与内涵,由此揭示出其中文字的机锋与文物之暗喻的双重奥义。这体现了沈从文先生深厚的功力:一方面有对文学作品的深透理解,一方面有古器物方面的丰富知识,以此方能参透文字中的“虚”与“实”。而虚实相间,本来就是古代诗歌小说一种重要的表现方法。这篇文字,实在应该推为名物考证的典范之作。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希望有人结合文献和文物来研究古代名著,并且直接提出了撰写《诗经名物新证》的课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初从孙机遇安先生问学,遇安师命我把这篇文章好好读几遍,说此文本身便是“名物新证”的范本。同时又拟了两个题目,即“诗经名物新证”与“楚辞名物新证”,要我选择其一,我选择了前者。《诗经名物新证》一书完成后,我曾在后记里写下这一经过,不过当时还只是刚刚入门,对“名物新证”的概念实在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认识,比如,为什么要重新起用“名物”一词?“新证”之“新”究竟在何处?新的名物研究与古器物学又有哪些不同?这些问题,我还没有想清楚。
逐步有了一点想法,是在写作《古诗文名物新证》的过程中。在此书的后序中,我大致总结了自己的基本研究方法,并且谈到了研究中经常思索的几个问题。之后不久,学友李旻为拙著《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写序言,其中提出了诗中“物”与物中“诗”的概念,这更使我想到:“名物新证”的理想目标,应该是用名物学建构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应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一面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诗中“物”与物中“诗”,二者原可相互置换,入手的角度相异,方法和目的却是相同的。我希望用这种方法能够使自己在“诗”与“物”之间往来游走,寻找它们原本就是相通的路径。
先说诗中“物”。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的写作,通常落墨于名家和名篇,亦即从艺术角度来看是属于文学之精华的部分。但同时,我们是否还可以有这样一种角度,即通过对诗中之物的解读,触摸到诗人对生活细节的观察与体验,揭示出物在其中所传递的情思与感悟?由此,一些在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视野之外的作品,也能体现出一种文心文事乃至彰显出诗意的丰沛。
于是,我想到应该先把我所关注的“物”与咏物诗稍作区分。咏物诗之物,是普遍之物、抽象之物;而我的研究对象,更明确一点说是近年我主要关注的两宋诗文中的物,是个别之物、具体之物。这些“物”,分散开来,是一个一个的点;把散落的点连接起来,便成一线,构成一部生活史细节的文学叙述史。“物”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关注,被书写,而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诗的艺术性,文字、格律、节奏、意境、意象等固然是其要素,然而用“格物”之眼贴近文学,或者也可以成为一种研究方法。
再说物中“诗”。今天的所谓“名物研究”,主要是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说得再直白一点,便是发现、寻找“物”里边的故事。它所面对的,是传世的出土文物;它所要解决的,首先是“定名”。我以为,对“物”,亦即对历史文化遗存的认识,便是从命名开始的。当然,“定名”不是根据当代知识来命名,而是依据包括铭文等在内的各种古代文字材料和包括绘画、雕刻等在内的各种古代图像材料,来确定器物原有的名称。这个名称,多半是当时的语言系统中一个稳定的最小单位,包含着一个历史时段中的集体记忆。而由名称的产生与变化,便可以触摸到日常生活史乃至社会生活史的若干发展脉络。然后是“相知”,即进一步明确此物的用途与功能。它要求我们有对艺术和艺术品的感受力,能够从细微之纹饰去辨识气韵和风格,把握名与实发生变化的因素,以及变化因素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文物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作为原初的“物”,即在被使用着的时代,它一面以它的用途服务于时人,一面也以装饰、造型等审美因素愉悦时人的目光。其二是作为“文”物,它承载着古人对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营造,有了更多的文化意味。“名物新证”应以历史的眼光,辨明文物的用途、形制、文饰所包含的“古典”和它所属时代的“今典”,认出其底色与添加色,由此揭示出“物”中或凝聚或覆盖的层层之“文”。同样是以训诂与考据为基础,新的名物研究与旧日不同者在于,它应该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完成一种贴近历史的叙述,而文献与实物的契合中应该显示出发展过程各个阶段的变化,此变化须有从考古学获得的细节的真实与清晰。
回过头再来看古名物学和古器物学,可以说,名物学是持“名”以找物,器物学是持“物”以找名。名与物的疏离处是二者各自的起点,名与物的契合处则是二者最有意义的殊途同归。而新的名物研究便是从这两个传统学科中生长出来,复由考古学中获得新的认知与新的方法——不仅仅是考古材料,而更在于考古学所包含的种种科学分析。
总之,“名物新证”所追求的“新”,第一是研究方法——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考古学异军突起,为名物学的方法革新赋予了最为重要的条件。第二是研究层次的深化以及研究内涵的丰富——由单纯对“物”的关注发展为“文”“物”并重,注重对“物”的人文意义的揭示与阐发。今天的名物研究,应有古典趣味之外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观照。它的视野里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细节,若干久被遮蔽的史之幽微,亦是研究过程常有的发现。一叶障目不可取,一叶知秋却可以也应该作为“名物新证”的方向与目标。对我来说,这样的考证过程永远有着求解的诱惑力,因此总是令人充满激情。
总之,定名与相知,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定名是针对“物”而言;相知,则须出入于“物”与“诗”之间,以此打通二者之联系。我把它作为研究工作的目标,也用它来检验自己的成绩,同时更希望读者也用这个标准来检验我的著述。今收在《棔柿楼集》中的卷十,便是我近20年来有关名物考证之著述大致分类的重新编订,大多注明了最初刊发的时间。具体情况,在每一卷的后记里也都有说明。
《文心雕龙·史传篇》第一节说:“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时古,其载籍乎。”刘勰的时代,欲接通古今,惟有文献一途。然而现代考古学的创立以及逐步走向成熟,却为我们走进古代世界揭示了更多的可能,也完全有条件使几乎被遗忘的名物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相关链接:
首届海南“最美书店”评选揭晓 7家实体书店登榜盘点那些不容错过的书店
处处飘书香 城市提气质(全国文明城市巡礼)
让更多人拿起书(记者观察)
·凡注明来源为“海口网”的所有文字、图片、音视频、美术设计等作品,版权均属海口网所有。未经本网书面授权,不得进行一切形式的下载、转载或建立镜像。
·凡注明为其它来源的信息,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601fd52f-7ef9-4ae9-bcd8-eea55e5b02ff_zsize.jpg)
4d74077e-60a4-4fe3-ba1b-afc1e75b7777.jpg)
8cedda49-fb53-4fc4-af03-f5688a426a6e.jpg)
bc829a93-57b8-4fdd-961e-5343278d0a5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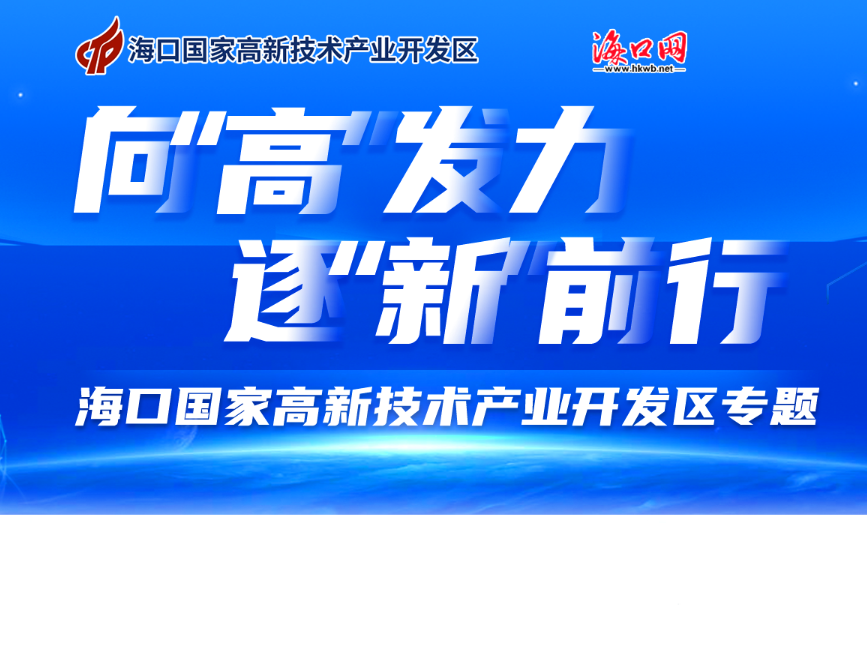


edef585a-fede-4ca8-bfa9-10e036755de3_zsize_watermark.jpg)


4f9ab47a-5c5d-4d6f-815f-8ccdbd4775e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