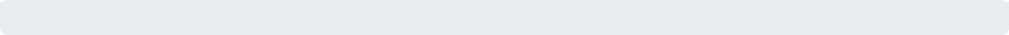当父亲遇上母亲(1) 新概念作文大赛
海口网 http://www.hkwb.net 时间:2012-05-07 17:14
母亲二十一岁那年从云南来到河南,来到父亲的家。
是父亲开着一辆老解放牌货车去接她来的。车轮子一公里一公里地轱辘到云南,又一公里一公里厚厚实实地轱辘回来。父亲在去云南之前,在村里李爷那儿筹了二百多块钱,全买了鞭炮。于是,十九年前,有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脆脆亮亮地从云南一路不绝响到了河南。
我时常想,那绵延一千多公里的鞭炮声,是我灵魂深处最动听、最深重的音乐。
父亲的一生坎坷多舛。小的时候家里不是一般的穷,父亲说他小时候吃得最多的东西不是红薯面,是苦。苦难在他的名字上也留下了烙印,他叫湘,因为他是在湖南逃荒的路上出生的。
但他是个汉子,无论多大的苦难都被他踩在了粗大的脚掌下。他的鞋子是四十四码的,身躯是弱不禁风的,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后来被家乡的夕阳镀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金色,他开始变得硬朗,肌肉也结实起来。
人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是能按自己的活法儿活——这是最大的惬意。父亲说。
我听爷爷说,在那动乱的十年里,父亲因为倔着性子不肯抓了狗屎往他高中老师的嘴里塞,而被红卫兵——他的同班同学拿了狗屎砸在了他的头上,他仍不屈,夜里挖了两块红薯烤熟了给老师当饭;大学毕业后,父亲没有按着分配的工作到乡政府去上班,原因只是他不想整日坐在办公室里发呆喝茶看报纸再发呆——那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
父亲坚持回家务农,他想自己干出点名堂。奶奶因为这事气得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
两年后的一天,爷爷的一个把兄弟李爷从县城回乡,开了一辆212吉普。那年月吉普车还是个罕物,看得村子里的小伙子大老爷们眼神都直耿耿的。
父亲经不住几个农伴的怂恿,偷拿了车钥匙,凭着自己大学里学机械制造提供的虚胆,打开了吉普车的车门。
海口网 http://www.hkwb.net [来源: ] [作者:] [编辑: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