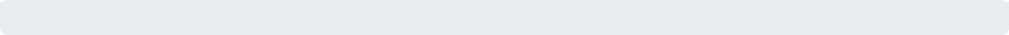深圳童工被送回老家 求记者别拍怕再打工没人要

在村小的教室里,吉觉阿呷帮低年级学生削铅笔。 记者 张文摄

吉觉阿呷的家。 记者 张文摄
“打工跟在家不一样吗?都是做事”
门外的大风不时地裹挟着黄沙呼啸而过,吉觉阿呷(化名)仔细地将上衣最上面的纽扣扣好,然后便背着背篓出了门。
回到村里已近一周,跟出去打工前相比,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在家哪一天不是这个样子,喂猪、洗衣服、生火做饭、背起背篓去找柴。”吉觉阿呷自顾自抱怨着,突然问记者:“在外头打工跟在家哪里不一样?都是做事。”
十几天前,因被怀疑是童工,吉觉阿呷和72名彝族同伴被大巴车从深圳送回凉山。
吉觉阿呷今年14岁,在家里的4个孩子中排行第二,常年在外打工的父亲在去年6月便去了广东,一起出去的还有16岁的姐姐。
吉觉阿呷告诉记者,她是去年11月后才出去的,但没想到刚在深圳工作几天,1月2日就被送回了村里。她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被送回来,“过了新年我就出去挣钱了,反正有妈妈看着两个弟弟。想不到这么快被送回来。”
有村民告诉记者,彝族新年是在每年阳历的11月中下旬,新年结束后辍学在家的孩子就会陆续出去打工挣钱。小学没毕业就辍学的吉觉阿呷算是打工的孩子里比较“有经验”的,她告诉记者,深圳的很多工厂她都待过,“绕线、装箱、打包,我都会!老板说我能干呢!”她的语调中透着几分自豪。
吉觉阿呷的母亲马卡阿莎介绍,“老板”指的是带孩子们出去打工的工头,据说是邻乡的,名字叫克巴。“每当克巴来找工人,娃们都很乐意跟他走。”马卡阿莎说,村里好几个孩子每年都跟克巴外出打工。
为什么不念书?马卡阿莎的回答很简单:“念书费钱,女娃儿认几个汉字能说点汉话就行了。”
她跟记者算了一笔账:国家免了学费,但每学期起码一两百元的杂费,到村小走山路起码要一个半小时,如果念寄宿制的中心校,即使住宿免费,每个月也需要一百元左右的生活费。“4个一起念书,家里确实供不起,不如让两个女娃给家里帮帮忙。”马卡阿莎说。
“过节和来客时才吃点腊肉”
傍晚时分,吉觉阿呷背着一筐干柴回来了。“冬天冷,要烧火塘烤火,还要煮饭煮猪食,我在家每天都去多找一些。”她一边说着一边吃力地把背篓从身上卸下放到墙角。记者走过去一掂量,这筐柴少说有20来斤。
“阿呷最勤快,等到2月初种土豆,她也能帮忙开犁。”马卡阿莎告诉记者,这里的村民基本都种土豆,“8月收获时,100斤一筐,每亩能收30多筐,只可惜卖不起价。”马卡阿莎说,这里路不好,汽车开不进,只能等附近乡镇赶集时用马驮几筐去卖,但却连8毛钱一斤都卖不动,算上种荞麦、养猪,每年只能有万把块收入。
对于家里的生计,吉觉阿呷也很苦恼:“我打工的地方,土豆两块多一斤!我们却只能等土豆粉厂用六七角的价格收,收不走的就只有自己吃,去年收的土豆现在还剩一大堆。”她说,“地里刨不出钱,只能出去打工,现在哪家是单靠种地挣钱的?”
不知不觉到了晚饭时间,马卡阿莎留记者吃饭。主菜毫无例外是炖土豆,没有佐料,淡然无味。也许是因为记者的到来,马卡阿莎竟端出了一盘腊猪肉和圆根酸菜。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跟记者说,“平时家里来客少,过彝族新年的时候杀了一口猪,腌成腊肉后只是逢年过节和家里来客时才吃。”
“不要嫌土豆不好吃,种出来也不容易!等到2月开种的时候,土硬得牛都拉不动,而且要我们四五个人一起种才行。”吉觉阿呷卷起袖子,手臂上露出一道清晰的伤痕:“你看,这就是上次耕地时不小心被犁划伤的。”
“有带上百名童工的,一个月拿七八万”
尽管在将童工们从深圳接回后,凉山州当地政府已经为他们的入学提供了必要的便利,但吉觉阿呷仍然不愿去上学。“我听不懂老师讲课,去学校有什么用!”她说。
经记者好说歹说,第二天一早,吉觉阿呷答应跟记者搭村民的摩托去村小看看。村小老师吉子阿牛告诉记者,学校的两间瓦房,容纳了全校40多名学生,一二三年级一间,四五年级一间。“常有辍过学的回来读书,但很难跟上进度,甚至有十三四岁的来读三年级。”吉子阿牛说,学生们普遍缺乏汉语听说能力,数学课时他经常要用汉语讲一遍,再用彝语讲一遍。
“很多学生从小就跟着父母外出务工,虽然小孩子没人敢用,但他们在打工的地方也入不了学,成了野孩子。”聊起辍学问题,吉子阿牛叹了口气。他告诉记者,去新疆摘棉花、去广东等发达省市等都是凉山外出务工人员热衷的去向,很多孩子跟着父母出去后,在打工地不能入学,耽误了学业,年龄稍大后学业更跟不上,外出打工似乎成了最佳的选择。
“由于文化水平不足,甚至汉语都不流利,完全不能融入外面的社会,他们出去只能做一般劳动力,挣得很少,所以有的人后来又想回凉山念书。”吉子阿牛说,在凉山甚至有20多岁的六年级学生。
而受益于辍学打工的庞大人群,一种新兴职业产生了:一些在外打工多年、对劳务市场“行情”较熟悉的打工者通过组织同乡辍学学生外出打工,从中抽取费用而牟利,这些人即为“工头”。
记者辗转联系上的一位“工头”透露,广东一家工厂给童工的工资为11元/小时,加班时为12元/小时,但由于工资由他代领,他发给童工的工资一律为8元/小时,按童工每天10小时的工作时间,“工头”每天可从每名童工身上抽取至少30元。
“我知道有带过上百名的,一个月可以拿七八万。”这位“工头”坦言,他最多一次带过50多人,其中大部分在16岁以下,劳动监察部门一般都查不出来,“跟工厂或者中介公司一起造一些假的身份证号就行,广东这边这么多厂,很容易就混过去。”
另外,这位“工头”也承认,他虽然一开始都许诺带着孩子们“挣大钱”,而且童工们每月也确实拿到大概2000元左右工资,但他们却很少有人能存下什么积蓄,“都是群孩子,走出大山后好奇心重,拿了工资后请客吃饭、买这买那的,能存多少?碰到黑工头直接吃他们的钱,那更惨。”
尽管如此,吉觉阿呷还是希望能出去打工。记者给她照相时,她敏捷地躲开了。“你拍我是要上电视的吗?不要让我上电视,不然出去打工他们就不要我了。”吉觉阿呷恳求道。
凉山正入户核实童工情况下学期将安排入学
从深圳童工案中解救回乡的孩子,已回到凉山10多天,他们情况怎么样?今日,记者从凉山州委宣传部获悉:当地政府成立了由劳动、宣传等部门组成的综合工作组,专门负责后续处置工作。
目前,工作组正在入户核实。据初步掌握的情况看,73个孩子中,16岁以下的有12个。但更进一步的情况,工作组宣传负责人表示“无法回答”。
随后,记者又致电凉山州教育局了解到,由于临近期末,被送回来的孩子暂无法入学。下学期,各县教育局将根据他们年龄段安排入学。
记者手记:破除困扰凉山“童工”的贫困怪圈
这里虽名为“凉山”,却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热土。
1956年凉山彝族自治州通过民主改革,实现了从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一步跨千年”的飞跃;2011年,凉山州经济总量突破千亿,居全省31个地市州的第七位,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4.4%;州内市县西昌、会理先后跻身中国西部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县市之列。
然而,作为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截至2013年8月,凉山州还有贫困人口108万,超过全州总人口的23%。近年的“彝家新寨”等扶贫工作使凉山州数以十万计的彝族同胞摆脱了贫困,但复杂的地形和自然、历史条件,仍然在制约着凉山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记者曾数度深入凉山采访,在这个彝族人口近半数的地区,处处能感受到淳朴的民风和好客的热情。但同时,吸毒、辍学等问题的存在,加剧了州内部分地区的贫困程度。
贫困—辍学当童工—回乡—贫困—再当童工,这个怪圈困扰着凉山州,极大地阻挠着这里的发展。贫困问题不是短期能解决的,提高凉山的总体人口素质才是关键。曾经有在凉山支教的志愿者告诉记者,只有让凉山的儿童走出大山,了解外面的世界,他们才可能从困扰父辈们的贫困怪圈中走出。而要破除辍学儿童一心只想外出打工的现象,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所幸的是,凉山的儿童从不缺乏关注,官方和民间的援助力量一直在为凉山的义务教育普及而努力。据凉山州官方数据,早在2012年底,该州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98%以上,彝语和汉语的“双语”教学也在大力普及。
因此,记者更希望,此次“童工”事件仅仅是一小段插曲,但愿这段插曲会引起更多的部门和个人关注凉山的教育问题,让这一屡见报端的顽症得到彻底解决,让凉山孩童的未来不再冰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