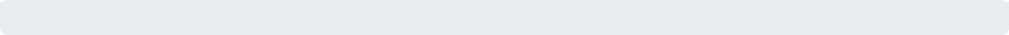湖北宣恩县一间学校仅老师和学生两人(图)

汪文强跟2个孩子在藤椅上玩耍。学校还有4个学前班孩子,是家长托赵国清照看的

4月1日,湖北省宣恩县珠山镇天井堡小学,赵国清正在指导学生汪文强做作业。一师一生,这所小学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一位老师,和他唯一的学生,是天井堡小学的全部。
这所武陵山区的学校,藏在湖北恩施珠山镇一个半山腰里,1000平米的校园荒草丛生,一条脖系铃铛的矮脚黄狗时常闯进两个人的课堂。
赵国清是天井堡小学唯一的老师,也是“校长”兼“伙夫”。
“普九”的时候,天井堡小学一度要换个名字,最后研究出4个字:育才小学。
繁盛时,也有几百个孩子在这里上课。打工潮兴起、撤点并校,山里人涌入城市……一切都在变化,到现在,这座小学已无才可育。
赵国清的一生正在经历农村教育不可逆转的变革:2012年一份教育研究报告显示,2010-2012年间,在中国平均每天就有63所农村小学消亡。
赵国清成为留守者,寂静对他而言已成了习惯。他的坚守,让这所只有一个学生的小学有了存在下去的理由。
【人物简介】
赵国清
59岁,湖北省宣恩县珠山镇天井堡小学校长,兼任语文、数学老师,伙夫。从教39年,如今,他的学校里,只有7岁男孩汪文强一名学生。
65和1
8:40,到校。
听到雨鞋磕碰地面发出的“嗒嗒”声,赵国清知道,学生汪文强到了。
4月的早晨,山里的雾还未散去,屋里寒气逼人,赵国清打开了小电暖炉,微光初亮。
一所学校,一位老师,一名学生,一间教室。
这里甚至算不上一间严格意义上的教室。
村里筹了款正在整修原来的教室,课堂临时搬进学校对面的村委会办公室。
摞起的办公桌椅堆满了半个空间,另一半,黑板架在办公桌上,裸露出大片白色,摆放歪斜的课桌后是电磁炉和碗筷,显得凌乱。
因为记者的到来,赵国清好不容易找到了人搭把手,将角落里的一台55英寸交互式电视一体机挂在了墙壁上。
这是去年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送来的,还有1台电脑,1架钢质讲台,因为学校整修,始终没安装。
除了开关机,赵国清不能完全掌握这台机器的其他用途,他知道要插上配备的U盘,点击教学视频,但机器仍然发不出声。他希望有外面的年轻人来教教他。
汪文强的课桌在教室最后一排,红色桌椅。前边两排,是4个学前班小孩的位子。
他们都不算真正的小学生:家长把还没到学龄的孩子送到天井堡小学,委托赵国清帮忙照管。
教了39年书,赵国清亲眼看着山里的小学一天天凋敝,但他从没想过,有一天竟然只剩一个学生。
2000年,他从山脚的狮子关小学来这当校长,还有60多个学生,校园里满是孩子唧唧喳喳的声音,清脆得很。
彼时的中国,正经历一场“撤点并校”的浪潮: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
“浪潮”里的天井堡小学已不是完小,只保留了一到四年级。
2008年,30个学生;2012年,3个;2013年,1个。
如今的天井堡村辖区内,入学适龄儿童有66人,其中65个去了其他小学。现在,这所小学连二年级都没有了。
和国内千万个村庄一样,大山里的天井堡村也正在遭遇城市化浪潮的冲击:村里的青壮年为摆脱困顿,先行一步,挤入城市,把孩子们也带了去。
剩下的留守儿童里,稍微富裕的家庭,更愿意选择另外几所学校。“虽然远,但条件好,老师多。”赵国清无奈。
唯一的留守者是汪文强,一个7岁的男孩。“我们条件不好,去别处读不起。”父亲汪胜超说。
“我们俩”
9:00,第一节课。
赵国清扯了扯挂在农具上锈迹斑斑的铃铛,原本还在教室外和小狗嬉闹的汪文强,噌地起身,飞快跑进了教室。
安排好三四岁的“小同学”观看儿歌视频,赵国清在嘈杂声中开始对汪文强单独授课。
他的普通话有些蹩脚,声母“z”和“j”不能清晰区分,在教生字“专”时,发音更类似于“娟”。
一条矮脚黄狗不知怎么闯进课堂,脖子上铃铛的叮当声,混在一老一少的读书声里。
课堂更像一个私塾,并没有太多规矩可言;与其说是师生,赵国清与汪文强更像是一对祖孙。
2012年9月,汪文强第一次见赵国清时,还在爷爷的背篓里。
当年的第一堂课并不成功,倔强瘦小又被娇惯的男孩不肯和生人接触。
接下来的一年里,汪文强都要求爷爷坐在教室里陪着一起上课,不然就哭闹不止。
赵国清决定改变之前对待其他学生的策略:他开始陪汪文强一起踢球,给他削铅笔,出门前给他整理好衣服。
“温柔、极富耐心,难得有这样的老师。”村里人这样评价赵国清。
“我表现软弱些、细致些,是为了让他留下来。”赵国清说。
但有时师生也难免有摩擦,数学课就是例子。
写下49、56、87一串数字后,赵国清让汪文强到黑板前写下这些数字的读法。
“我不够高!”汪文强用方言喊了一声后,赵国清给他挪过来一只板凳,让他站上去写。
四九、五六、八七。
赵国清蹙起了眉毛,看起来像是压抑着火气:“咋个读滴嘛?中间的十咧?不见了?”
汪文强低着头,不言语。下课后,孩子的不愉快忘得一干二净,又挤到赵国清身边。
汪文强的课只有语文和数学,下课间隙,11点40分,赵国清当起了伙夫:把屋里的电磁炉和碗筷搬到教室外面,开始做饭。
大山里的岛
12:00,午休。
汪文强的午餐是赵国清准备的营养餐:胡萝卜炒肉,淋在一碗面条上。
赵国清清楚孩子的胃口,特意给他多盛了些胡萝卜片:“他不怎么爱吃肉。”
汪文强扒拉着面条,抬眼看着他前边三四岁的孩子们。
在赵国清眼里,比起之前的学生,汪文强更黏人,他经常向老师“揭发”学前班孩子的调皮行径,尽管他有时也是参与者。
“可能是没有同龄人陪伴,比较孤独吧。”赵国清叹气。
这孤独同样映射在赵国清自身。
因为不少媒体的来访,赵国清在珠山镇已经小有名气。住在学校旁的村长家给记者提供饭食,也请赵国清去作陪。
面对诸多陌生的成年人,饭桌上的赵国清有些局促,不怎么说话,也不太伸筷子吃菜。
几杯山里人自酿的包谷酒下肚,他才放松了些,黑脸泛红。
“我今年59岁,教了39年书,就快退休喽。”
珠山镇的驻村干部杨谊在他身后摇头,轻轻叹息:“年轻老师都不肯来山里,你还要教娃哦。”
没有年轻老师愿意来,这是天井堡小学面对的现实。
在宣恩县,像天井堡一样的“微小学”散布在大山里的各个角落,像一座座岛屿,与外界隔绝是常态。
天井堡附近的铁厂坡小学和茅坝塘小学,都是一个老师,6个学生;荆竹坪小学,5个学生。
杨谊想起几年前,年轻的老师到茅坝塘教书,笑着到来,哭着离开,他们忍受不了孤独。
还有支教的老师,宁愿每天来回坐几个小时的车下山吃住,但也只坚持了一年。
“一天除了学生,见不到一个人影,只能跟空气交流,咋不走。”杨谊说。
赵国清是少数坚持下来不走的人。他说他习惯了这里的宁静。
在“孤岛”活了一辈子,赵国清已经不擅长和学生、家长以外的人打交道,尽管他有时要履行校长的职责。
其实这种履职,更多也只是通过电话,教学点所属片区的校长在电话里对赵国清上传下达。
去年10月,赵国清去了狮子关小学,为了给汪文强办学籍,让自己的学校还能称之为学校。
在人来人往的办公室,这位只有一个学生的校长,像小学生一样斜挎着包,涨红了脸,他不知该找谁,也不知怎么开口。
未来
16:00,放学。
赵国清希望汪文强能在这读二年级,即便只有他一个学生。
如果汪文强离开了,赵国清将会面对无法预知的未来:4个学前班的孩子,不确定是否留在这读小学。
“如果一个孩子都没剩下,校不成校,我就该退休了,年纪也大了。”赵国清说。
一天的课程结束,小学门口,赵国清和汪文强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各自走向回家的方向。
他回头看了看汪文强瘦瘦小小的背影,忍不住叹气:“假如我的孙女也在天井堡小学读书,我应该还是教得不错的。”
赵国清4岁的小孙女,就读于30公里外宣恩县城一所幼儿园。
一个月前,赵国清的老伴带着孙女离开大山,到幼儿园附近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方便孩子上学。
每月460元的租金,快占了赵国清工资的一半。
但这是赵国清儿子儿媳的决定。
孩子上学前,赵国清就提出过自己来教的想法,但遭到儿子儿媳的一致反对:“就你一个老师,教学质量怎么跟得上?别人孩子都去城里读书,读小学时赶不上怎么办?”
没有任何争论,赵国清同意了:“儿女有儿女的考虑。”
其实他心里不服气。
当了一辈子老师,没有资格教自己的孙女——赵国清人生里唯一的成就感,正在被时代的变化渐渐消解。
“世界变化太快了。”他感慨,“我就要跟不上了。”
但他仍旧想培养出好学生,新来的学前班孩子就是他的希望。其中一个女孩,反应迅速,记忆力也不错,生字教过几遍就都能认全。
“她就算以后离开天井堡,去别的学校肯定也不会差。”赵国清有这个自信。
下了场雨,下山的路有点湿滑,赵国清搭上了一班顺风车。
前排的司机探头看了看后视镜,叫出声来:“你怎么那么面熟,是上过电视的那个老师吗?”
后座的赵国清嘿嘿一笑,腼腆地点了点头。
车很快到赵国清的家门口。这次,他站在路边不愿离去,和司机聊了起来:“我希望我在这里一天,学校就存在一天。再有就是我不在,学校还要存在。”
相关链接:
河北将把学生非正常死亡事故纳入学校考核小学推出30门选修课培养学生兴趣爱好
27岁医学学生患白血病去世 遗言志愿做医学标本
微软“创新杯”全球学生大赛 今年首次引入海南
PX词条被篡改为“剧毒” 清华学生捍卫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