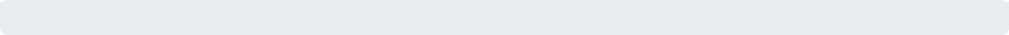墙洞上的孩子:沈阳流浪儿童半米高墙洞里安家(图)
方大爷打扫卫生路过时,总会提高嗓门,冲着洞口喊一句:“起床啦!”随后,他会看见洞口一块用来挡风的棕色胶合板被移开,3个小脑袋并排探出来。
提起墙洞里的“居民”,没有人比负责这个片区卫生的环卫工方大爷更了解了。
在他的记忆中,3个孩子里,最早搬到这个洞,过起“穴居生活”的是黄毛儿。
快要过18岁生日的他,也是孩子们当中年龄最大的。黄毛儿老家在沈阳一个县级市,进城已经两年,曾在汽车修理店当过杂工,也在一家饭店打过工,后来没了工作,流浪到火车北站附近。从去年开始,他住进了这个墙壁上的洞穴。
后来,只比黄毛儿小几个月的大个儿也来了,两个男孩一起分享这两立方米的空间。
上个月,7岁半的小宁也加入进来。
方大爷不止一次看到,为了攀上两米高的洞口,3个孩子把马路边的垃圾箱拖过来,斜靠在墙上,踩着垃圾箱“回家”。有时,两个大男孩也会后退几步,蓄力,助跑,沿着墙壁的斜面,“飞檐走壁”一般蹿上去,然后从洞口探出小半截身子,一起把小宁拽上去。
每天清晨,方大爷打扫卫生路过时,总会提高嗓门,冲着洞口喊一句:“起床啦!”随后,他会看见洞口一块用来挡风的棕色胶合板被移开,3个小脑袋并排探出来,自上而下地看着他。这个场面,方大爷觉得“老有意思了”。
军绿色的军用被,当作褥子平摊在洞里,向外铺出来一个边儿,孩子们扒着边儿趴着,把手臂撑在褥子上面,另一床花被子搭在身上。被子都很旧了,看起来有些单薄。
黄毛儿在胶合板上钻了个手指粗细的孔,更多时候,他用板子挡住洞口,猫在小孔后面,看外面来来回回的行人。
除了一名摄影记者,恐怕没有其他外来人得以窥探洞中的生活。这名记者曾爬进去拍摄洞里面的样子,没几下就把膝盖磕得青紫。他记得,洞里零星摆着一些东西,有瓶瓶罐罐,还有几双鞋。当时恰好是天热的时候,这个作为排风口的洞,发出让人反胃的气味。
“要是回家,我就得和我爸一起捡破烂。”方大爷曾听到小宁这样描述可能的未来。黄毛儿劝他:“别回去了,我们养你。”
尽管在同一个洞里“穴居”了很久,但据方大爷观察,3个“住客”似乎并不知道彼此的姓名。他们都是喊着“哎”、“喂”来相互称呼。
他们常在洞穴下面玩。一个清晨,小宁趴在洞里,黄毛儿骑坐在路边的垃圾箱顶上,他们笑眯眯地看着大个儿表演用嘴叼起一辆自行车的“绝活儿”。
无所事事时,黄毛儿时常耷拉着腿坐在洞口,和方大爷闲聊。从零零星星的对话中,方大爷得知,黄毛儿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与他父亲离了婚,11岁的时候,父亲也“抛下他走了”。他说,是自己“不要他们(父母)了”。
他比总是一身灰色、理着板寸的大个儿和小宁,显得更“时尚”一点:蓬松的头发,几撮刘海挑染成棕黄色,黑白花纹的外套上,印着菱形交错的图案,跑鞋上荧光绿的鞋带,远远看着格外显眼。
但相同的是,3个孩子身上的衣服,都同样脏得“锃亮”。
车站附近快餐店的一个店员告诉记者,3个孩子经常来这儿捡别人吃剩下的食物。
街口买饼的摊主说,出于同情,他偶尔会给他们几个饼子。马路对面的超市老板记得,从洞口经过时,他曾给孩子们塞过一些钱,也问过他们“为什么不找个工作”。
黄毛儿的回答是,自己本想当保安,但身份证弄丢了,户口“在爸爸手里”,他“不愿去找他”,所以身份证一直没有办下来。
同样17岁的大个儿是3个孩子里最高的,身高一米七出头的他,比黄毛儿高了半个头,常把瘦小的小宁扛在脖子上。
大个儿的情况和黄毛儿很相似,同样有一个早早就抛下他的母亲,不同的是,大个儿的父亲去年去世了,他已拿不准,自己要回的“家”,究竟在哪儿。
这个总是带着憨厚笑容的孩子,当过快递员,送过外卖,还曾被老板骗,一分钱工资没有拿到,就被赶了出来。
而3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小宁,把墙洞当成了一个隔三差五的歇脚处。
他家其实离北站并不远。在这间七八平方米的砖房里,占据房间一半空间的炕上,堆满了衣服和被子。砖房的前面,就是用棕红色土砖垒成的简易公厕,厕所门离他家不到一米,整个房间常年笼罩在恶臭当中。
小宁两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离开了这父子俩。白天父亲出去工作,把小宁自个儿锁在家里。小宁打破门上的玻璃,父亲就在门框上装了铁丝网,小宁又用老虎钳剪破门框上的铁丝,再次爬了出去。
起初他只是在附近玩耍,后来却越走越远,离家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原本焦急寻找他的父亲,慢慢习惯了这个儿子常年在外流浪。
父亲也想过,或许等这孩子“上学就好了”,但是,小宁是个非婚生子,都快8岁了,仍然没有出生证明,也没有户口。学校的大门似乎遥不可及。
他不愿意待在家里,宁可和其他两个“大哥哥”一起,挤在那个只有厚床垫大小的空间里。
“要是回家,我就得和我爸一起捡破烂。”方大爷曾听到小宁这样描述可能的未来。黄毛儿劝他:“别回去了,我们养你。”
就在他们栖居的墙洞对面的街上,恰好有一所小学,趴在洞口的小宁,如果向东远远地眺望,可以看到那所学校的教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