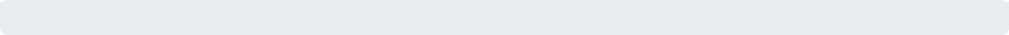揭秘性学研究:女研究生调查红灯区内心濒临崩溃

方刚给小学生讲解性教育展览(方刚供图)
那年,还在做记者的他偶然看到一条讲同性恋的新闻,在好奇心驱使下他去采访这群人。改变由此开始。
第一次访问是在路边的小饭馆,这群人大声地在餐桌上谈性。那是他第一次见识这样的场面,彼时已婚的他,面红耳赤的同时心脏狂跳:“那是1993年!是谈性色变的年代!我前面25年听到的性话题加在一起,再翻十倍都没有那天晚上谈的赤裸、直白!”
“原来性可以这样大大方方地谈!”轰然一声,他脑子中某个硬的东西碎了,伴随着内心隐约的快感。
在方刚眼里,这些同性恋者礼貌又热情,“除了他们喜欢男人,我觉得他们和我没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歧视他们?”他很快认同并接受了他们。
方刚出身“黑五类”家庭,三岁时,父亲自杀身亡,他的童年乃至青少年时期一直被欺辱,在想反抗又不敢反抗中度过。他太了解身为少数者、异类,被欺负被侮辱的感受。“我从三岁起,就一直是弱者、被歧视的人,所以我会本能地和性少数者这些社会性道德上最弱势、最边缘的人站在一起。其实做性学研究这行,尤其是关注性少数者权利的这些人,对主流、对大众的声音都是抱有警惕的。”
方刚认同他的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曾说过的话:“我们在讨论各种性的道德观念时需要认真地想一下:我所主张的性道德,究竟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总结,还是被别人潜移默化地灌输进来的?性道德究竟首先是用来协调我自己的,还是用来指责别人的?”
1995年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一书出版时,他在1993年采访过的几位同性恋者因为不堪歧视,已经自杀离世。
多年后,方刚和他的前辈学者李银河一样,成了性权派,提倡在不侵犯别人人权的前提下,每个人有自由选择性倾向、喜好的权利,“异性恋,同性恋,换偶,禁欲,群交……只要不伤害别人,都是平等的”。
他在自己开设的性心理学课堂上常对学生说:“你现在还很侥幸身为一个主流社会的异性恋者,但是你并不能保证你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他们都这样,你希望他们受歧视吗?如果你不希望他们受歧视,就从现在开始改变。”
“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少数,我们一定有某一方面是弱势的,比如秃顶、乙肝,如果我们内心相互歧视,那谁都免不了歧视。如果一个社会中最被污名化的性少数者,都能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那其他人也能免于被歧视的恐惧。我们所有人都能获得更自由更有尊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