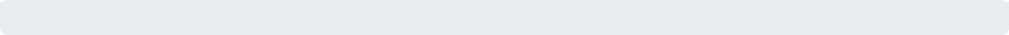北大教授病逝憾未竟功 学生回忆称其犀利仁师

北大教授、民族史学家刘浦江近日因癌症去世。学生称,刘老师细致缜密,擅长棒喝,“每次骂人都不重样”。同时,他温厚又不失可爱,视徒如子。重病时,他把未完成的书稿交待给学生,“未竟的事业有人传承,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刘浦江
性别:男
籍贯:重庆垫江
终年:54岁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身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辽金史、民族史学家
生前住址:海淀区大有北里小区
■ 逝言
告诉你们我为什么不畏惧死亡。一个人文学者,有一流的作品可以传世,能够培育出一流学者来继承他的事业,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顶多有一点遗憾而已。
不管大家以后从事什么职业,最关键的是,每做一件事情都必须全身心地投入。惟有如此,你才能成功,才能安身立命,才能获得尊严。
——摘自刘浦江给学生的学术信札
■ 生平
1961年 生于上海。
1983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
1988年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4年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政府特殊津贴。
先后出版《辽金史论》、《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契丹小字词汇索引》等著述,发表论文百余篇,部分文章被翻译成日文、英文。
其《辽金史论》获首届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二等奖和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随后,声明不参加任何奖项评选。
2007年至2014年负责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工程之《辽史》修订。
在北大,他是学生公认的“四大名捕”。为了不被他“骂”,多少学生勤学苦练,走上了学术之路。
他对学生的好是无声的。“浦江公”式批注,密密麻麻盖住了原文的字段。一晚上打几十个电话,为学生推荐合适的工作;给老友的邮件,全是推荐学生的论文。
手术后,他还在盘算,如果恢复得很好,就去学校上课;如果好一点,就把学生叫到家里来上课。
在生命的最后时日,他发信给学生说,“你们的工作没定,论文没改完,我放心不下。一定要继续努力,跟我在时一样。”
细致缜密,最擅棒喝
“他的词汇量大,每次骂人都不重样!”苗润博说,有同学直言,如果他“骂”的不是自己,“其实听着也挺精彩的。”
邱靖嘉是刘老师带的博士生,入师门第一天,他就眼看着刘老师连环炮式的批评,把一个师姐说哭了。
在做学术上,刘老师要求要句句落实、考镜源流、辨正讹误,该查的史料绝不能省。若是做不到,他脾气急,“会直接批评你。”邱靖嘉说,“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
曾上过刘老师两门课的陈恒舒回忆,在几年前的《四库全书总目》研读课上,刘浦江突然打断一个学生的发言问:“你是宋史方向的博士,《隆平集》该读过吧?”学生迟疑了一下,小声说“读过。”刘浦江抬高嗓门继续问:“读的什么版本?”女生顿了顿说:“中华书局点校本。”刘浦江又问:“中华书局出过《隆平集》的点校本吗?”答案其实是没有。
“他的词汇量大,每次骂人都不重样!”刘浦江带的另一位博士生苗润博说,有同学直言,如果他“骂”的不是自己,“其实听着也挺精彩的。”
对于历史系新人,每年开学,他拿着名单先问一圈问题。学生们一个个答不上来,他习惯挑起左眉,认真地说:“啊?连这都不知道啊!”然后再劝慰道,“咱不能坏了历史系的名声,咱得有点文化吧。”
作为“中文系同学最热爱的历史系老师”,2004年前刘浦江一直给中文系大一新生讲古代史。有学生回忆,整个学期刘老师都会很注意培养中文系学生的“古代文化素养”。学期末古代史要考干支纪年、读写繁体字等,也几乎成为每届北大中文系学生的集体记忆。
温厚笃实,视徒如子
两人讨论一个文献的引用,刘老师说你那个不好,是二手文献。苗润博立即反驳,那你那个还是三手四手的呢?刘老师听了没说什么,两人继续查证。
刘浦江曾说,“一个人能够有幸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是很难得的。找到了,就要全心投入。”在邱靖嘉看来,刘老师性情温厚,但又不失可爱。
苗润博跟着刘老师学习5年,他本不是北大的学生,大三时来蹭课,课后找到刘老师说“我来就是为了挑出你文章中的一处错误”。没想到因此被招至门下。
刘老师心细,知道苗润博需要往返北京、天津两地,特意让师兄告诉他,尽管来听课,不用担心往返费用。
但平时苗润博还没少跟老师“叫板”,两人讨论一个文献的引用,刘老师说你那个不好,是二手文献。苗润博立即反驳,那你那个还是三手四手的呢?刘老师听了没说什么,两人继续查证。
刘浦江说话有一个特点,经常前面好好的,突然来个“大转折”。有一次苗润博在阅读典籍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刘老师当时激动坏了。“能把这个问题做出来,将是这个领域的重大突破。”一句话把苗润博说得热血沸腾。“但是,”大转折来了,“如果你的写作能力提高不了,很多好问题都无法圆满完成。”
“他爱打这部研究中心的电话。”苗润博介绍,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最西面的一间,是刘老师的办公室,师门弟子每人一把钥匙。谁在这里接到老师的电话,总能聊好一阵,“就像父亲一样聊。”
在这个办公室,苗润博总想到,师兄弟们围坐在刘老师旁边,一起吃零食,聊天南地北的学界趣事。这时候的刘老师眉飞色舞,坐在椅子上转来转去,“和做学问时判若两人”。
“他爱吃冰淇淋。高兴时带我们下馆子,吃完必须加个冰淇淋。”苗润博想起来,“我们常说,到了七八十岁,他一定是个老顽童。”
黎明痛哭,只为遗憾
保守治疗可维持生命,干细胞移植可能治愈,但风险也大。他选择了后者,“与其苟且地活着,不如尊严地死去。”
确诊为淋巴癌晚期的消息,最初是瞒着他的。
从重庆回京的晚上,刘浦江得知了自己的病情。他当时很平静,说好第二天去住院。然后回到书房,整理书和笔记,哪些没有做完,需要交待给学生;哪些书对学生有用,给他们都分一分。未毕业的学生,未修改完的论文,未完成的书稿……
他房间的灯,一直亮到第二天清晨。
“我从没见他哭过,那天早上他放声大哭。”女儿刘以皙明白,父亲把很多东西放在心里。
那个清晨,刘浦江对女儿说,以后你要照顾好母亲。“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选择一个人,就要过一辈子。不然,一个人也能过得幸福。”
从此,他仿佛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再没有为疾病表现出痛苦。化疗期,他经常低头不语,“咬着牙关忍”。
治疗期间,只要不发烧,他就给学生修改论文,修改“辽史”文稿,去年5月,他还给学校提交了下学期要上的课程。
两次化疗后,他面临选择。保守治疗可维持生命,干细胞移植可能治愈,但风险大。他选择了后者,“与其苟且地活着,不如尊严地死去。”
在去年5月27日给学生的邮件中,他说,明天你们就要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了,遗憾的是我无法参加。本来很想在你们毕业典礼那天,与身穿博士服的你们一起合影,可惜难以如愿了。如果那时我在家,你们可以来我家合个影,不过我的头发已经快掉光啦。
去年12月,癌细胞全面复发,干细胞移植手术失败。刘老师已不能下床,戴上呼吸机,决定第二天回重庆老家。
临行前,师门弟子一个一个跟老师告别。看着面前泣不成声的学生,刘老师气息微弱,戴一会儿呼吸机再拿掉跟他们说几句话,“已经半年了,该有思想准备了,不要耽误我说正事。”
弟子们回忆,最后,刘老师交待了未完成的书稿要我们继续完成,把在读的师弟们安排好。嘱咐已经工作的师兄,以后师弟们毕业找工作时要多帮助。
从医院回来,想起老师行前托付,一位学生深夜睡不着,给老师发了一条信息:您未完成的研究,我会尽力完成。
第二天,刘老师回复,“我未竟的事业有人传承,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 寄语
他家的电话,是我最熟悉的号码之一。多少次他深夜还来电话,所谈所想,无不是系里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学生指导。说到学界的人和事,他头头是道,如数家珍。我们都知道,这一切,直至今日,都让他割舍不开。
浦江,你的坚持,你的理想,时刻都在我们心中。放心走吧,天国自有读书处。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邓小南
我在北大的七年,从入学到硕士答辩毕业,刘老师出席了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在毕业答辩后,我哭得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事后有同学告诉我,当时刘老师一直笑着看着你。
不知道刘老师现在是不是又在什么地方笑着看着我,看着我们。我,我们,都想请您继续看着,您的期待,我们对您的承诺,一定,都会实现。
——学生李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