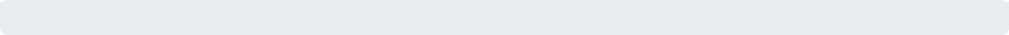生如夏花:乳癌患者的康复手记
让癌细胞也不敢往里闯
“英子姐,我觉得尽管你比较内向少言,但骨子里挺大咧的,不是那种较真儿的人啊。”我不禁发问。
通过将近两年与诸多乳癌女人的沟通接触,我发现一个未经确证的规律:为人处世越是大大咧咧,对病情的康复就越有利。即便之前是敏感多虑的性格,只要患病后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自己不要凡事必须来龙去脉分明,对于战胜癌症会有极大的帮助。多思多虑会让人处于紧张的状态,不如难得糊涂傻乐呵傻美,放松心情选择愉悦地生活。越是这样的患者,越容易真正重生。
英子姐给我发来了微笑和鼓掌的表情,显然是很赞同我的观点,而她后边的讲述更印证了我之前的判断。
不知道又过了多久,英子姐感觉到有人在移动她的肢体,稀里糊涂的地喊了一句:“我困死了。”
“医生说还有一点没弄干净,再进去一会儿就好了。”是常林贴着她耳边低语。英子姐身在云里雾里,任由他们把自己又搬到手术车上,只记得二姑姐在旁边都哭出声了。至于怎么进的手术室,怎么出的手术室,期间经历了什么,她一概不知。
英子姐是在深夜被疼醒的,那时没有镇痛棒,麻药退后的那种痛彻骨髓的折磨,她如今都不愿意去回忆。手术的前几天,医生曾经开过一张条子,到国药老总那里特批了十支杜冷丁,交代过:不是很疼的时候不要打,会上瘾,对伤口也不好。
“当晚全家总动员,二姑姐负责照料,大姑姐负责送饭,比前几年生孩子的时候待遇都好。老公更不用说了,时刻守在身边,看见我疼得直冒汗,牙齿把嘴唇咬出血,他们就商量给我打一针杜冷丁,但被我拒绝了。之前有一个熟人,就是用杜冷丁治疗胃痛最终导致吸毒的,这个事件在我心里印象太深刻了,我宁愿忍受痛苦也不愿意染上毒瘾。就这样痛一阵晕一阵,反反复复好不容易挨到天亮,也许是天亮带来的希望,似乎疼痛也减少了些。”隔着屏幕,我感受到英子姐的嘴角露出笑意,“肚子开始饿了,一碗粥下去,渐渐有了力气。努力对老公露出一个艰难的笑容,铁骨铮铮的汉子眼圈红了,回身抱住自己的二姐哇哇大哭起来。多年以后,二姑姐提起那个夜晚的时候,眼里还总是闪着泪花。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切除了乳房,成了‘少奶奶’。”
英子姐第一次知道自己失去了乳房,是在转天医生查房换药的时候。医生打开如五花大绑的绷带,她瞬间感觉到身体重量的偏失,右侧胸部凉飕飕的,就像是大风来了,没有遮挡的大门直接被寒气逼近一样,英子姐觉得自己的骨头直接对准了空气。她使劲儿低下头,去观察自己的患侧,看到的是一片狼藉。她傻愣愣地问常林:“我的……胸呢?”常林像个孩子似的哽咽着握住她的手,没有回答,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没就没了吧,有命在就行。我要活着,我得陪你和儿子过日子,得给公婆养老送终……”英子姐摸摸老公的脸,帮他擦了擦眼泪,非常虚弱地又闭上眼睛。
当时只有二十七岁的英子姐绝对是非常有韧性的女人,身体的缺失在她这儿真的不算事。我曾在医院看到过五六十岁的患者,因为失去了乳房还会哇哇大哭的,而年纪轻轻的英子姐只有一个信念——和家人一起好好地活着,对于其他,没有一丝纠结。
在整个住院期间,英子姐都沉默寡言,只是按照医生的要求多吃多睡,准备迎接化疗。直到病理下来,她才再次感觉五雷轰顶。病理结果并不乐观,淋巴结转移了八个,病理分级为中晚期。
那时候的互联网尚未兴起,关于乳癌的各种信息也鲜有资料可以查询。但英子姐还是从大家带着遗憾的表情中明白了一件事——自己的病原来很严重。
“医生,我到底还能活多久?”英子哭着问。
“这个不好说,尽管中晚期相对而言不容乐观,但有医学奇迹的发生也说不定。毕竟该切的肿块都切了,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你的身体里已经没有癌细胞了。”医生回答得很婉转,但也很客观。
英子姐一下子就舒心了很多,可能是这些年的生活中遇到的都是善良的好人,她愿意把一切往好处想。既然很多中晚期患者也都能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自己不是其中那个让死神绕路而行的人呢?
那年的春天雨水很多,英子姐拿到病理结果的那一天,又是暴雨倾盆。伴着窗外豆大的雨点猛烈敲击玻璃窗的声音,她性格坚韧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英子姐对常林说:“这张纸你收着吧,要不是医生说必须留着,我现在就把它烧了。反正我是不想再看一眼了,省得每看一次,都提醒自己一次——癌症中晚期。爱什么期就什么期吧,我认定了,该去的肉去掉了,毒瘤就没了。人这一辈子,一切都有命数,该活死不了,该死活不长,既然毒瘤都没了,那我肯定就死不了。以后谁都别拿我当癌症患者,咱们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英子姐是这么想的,也是这样坚持的。转眼到了深冬,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她已经戴着婆婆亲手织的红色毛线帽子直接上班去了,一张因化疗副作用而浮肿的脸上写满了平静。
领导劝道:“再休息段时间吧,毕竟是……”
英子姐听得出画外音,那省略的分明是癌症两个字。癌症与死亡有多近?恐怕上帝都不可能有个准确的定论。
英子姐摇摇头,轻柔地说:“谢谢您的关心,我现在是正常人了,就应该过正常人的生活,上班,下班,回家,做饭,晚上和老公孩子一起看电视,周末和两个大姑姐一起陪伴公婆,参加同事的聚餐,赶上忙的时候,该加班就加班,总之,就是以前什么样儿,以后还是那样儿。我不需要刻意的照顾,大家也别把我当作特殊的人物,我少了一个乳房不假,但我的手我的心我的脑子还都在。我必须尽快工作,生病可是花了不少钱,我得帮家里承担一些。”
领导是个老大姐,听到英子姐这么说,眼圈当时就红了:“总得照顾一下你呀,有什么要求就提,看看大家都能帮点什么?”
“真的没有。如果非要说,那就只有一点,希望大家忘掉我生病的事,即便是出于关心。因为我自己已经忘了。”
老大姐含泪连连点头。她答应了,也确实做到了,自打英子姐恢复上班到现在,二十年来,从没有人问过她那段手术治疗的经历,也没谁有意无意地盯着她的胸部看。乳房切除之后,英子姐就不再穿胸罩了,以小背心替代,让自己的胸部彻底解放。但没有义乳的掩饰,会很明显地从外部看出缺失了一个乳房,英子姐自己毫不在乎这些。她只在乎每次复查时候医生的回答——没有问题,一切都好。
“最初复查紧张吗?”
“不紧张,那怎么能叫紧张呢,简直是吓得要死!”英子如实回答。
“什么时候开始放松了?”我继续问。
“到了第四年吧,应该差不多是第四年。”英子很努力地回忆了下,“最初的几年,尽管我不跟任何人说,包括常林,但其实每到快复查的那段时间,我都莫名心慌,从里往外地烦躁,甚至依靠打坐来控制这种慌乱的心绪。可到了第四年的时候,忙忙碌碌地竟然忘记了复查的日子,等我马不停蹄地赶过去,医生还是那句,没有问题,一切都好。等事后一想,是啊,自己哪里不好了?到了第五年,不需要每半年一复查了,我就正常地跟着单位去体检了。一来二去,不需要强迫自己忘掉生病的事实,甚至对空荡荡的右胸也见怪不怪了。这大约跟我很小就就在外上学,一个人形成的特别独立的性格有关系。”
“总得有排解自己的方式吧。”我想知道英子姐有什么诀窍。
“忙啊,呵呵。”英子姐不假思索地说,“如果非得找到一个排解的方式,那就是忙碌起来。忙工作、忙家庭、忙学习,一天到晚时间满满的,哪里还有闲暇琢磨病情?那么多‘忙’字写在我身上,癌细胞也不敢往里闯了。呵呵,死神就算来了,我也得让他等我忙完了再说。估计他也觉得无趣,便真的绕路而行了。”
“除了正规的治疗,也没有用一些其他的办法吗?”我还是不死心,总想问出些秘籍。
“没有啦。”英子姐笑着摊开手,继续说,“我婆婆倒是到处找偏方,我也不好违逆老人的好意,就假意应着,以各种借口阻止她陪着去,答应她我会和常林去。不过每一次,我俩都是要么看电影,要么逛公园,实在不行就在市场转一圈再回家。倒不是不相信那些偏方,只是不想让自己沉浸在对病症的纠结里。这么多年来,海参啊孢子粉啊鹅血,我一样也没尝试过,更没有过自怨自艾和患得患失。正常生活,这就是我好好活了这二十年,让死神绕路而行的最好办法。”
正常生活,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种极高的境界,有多少人能在顺风顺水的时候保留正常生活?又有多少人能在命运多厄的时候坚持正常生活?正常生活又指的是什么?清晨轻推开窗子,让新鲜的空气进来,之后在匆匆上班的人潮中行走,挤公交乘地铁,吃着街面上最家常的早餐,在熟悉的环境里做八小时的岗位工作,晚上下班回到家,做饭吃饭,一家人其乐融融。有多少人能够热衷于这样的正常生活?有多少人能把没有变化的每一天当作是一种幸福?二十年前以为死神临近的英子姐,每一天都感受着这种毫无变化的生活所带来的幸福感。
这应该是英子姐二十年来第一次对别人讲述那段过往,是我让她平静的生活又起了涟漪。但英子姐很坚定地否认了,她笑着说:“还以为自己的情绪会有很大波动,而实际上没有,二十年来我真的已经习惯了。请原谅我之前的顾虑,也谢谢你让我有机会一吐为快,能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做一次总结。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更没有预知的可能,既然来了,就接受现实,接受得越彻底,命运的转弯越会意想不到。就像我,从以为死神临近,到让死神绕行,看似用了二十年,其实,就在我术后接受了一切的瞬间,便已经确定了这样的走向。”
最后,我和英子姐愉快地约定,等再过二十年,我们一定再好好聊聊。
二十年!是的,每一个乳癌女人都要有信心再活二十年,第二个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