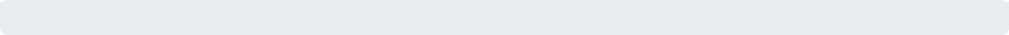柴静童年可爱照曝光 书香门第背景揭秘(图)
近日,有网友曝光了一组柴静的童年青涩照,三好姑娘可爱的姿态一览无余。
1976年,柴静出生于山西晋南的小城临汾,住的是祖上传下来的大宅子。父亲从医,母亲执教,可算是书香门第。柴静家在当地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曾祖父是个秀才,整个家族都住在从祖上传下来的一座有300多年历史的大宅子里。柴静至今还记得童年时喧嚣热闹的气氛、雕花窗棂、木制油伞和那些古色古香的家具。
柴静的妈妈是个坚强独立的女人。由于姥姥去世的很早,年幼的母亲一直担负起家中的大小事务,除了为姥爷和舅舅做饭洗衣服之外,还要刻苦读书。那个时候,母亲的成绩一直都十分优异。在母亲17岁时姥爷突发心脏病去世,当时,舅舅正远在外地念书,为了不耽误舅舅的学业,是母亲一个人强忍悲痛处理了外公的后事。19岁那年,柴静的母亲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师,此后不到10年,因为教学业绩突出,她被评为山西省第一批特级教师,不久又被任命为临汾某小学校长。在这期间,柴静的妈妈结识了善良执着的父亲。
在柴静的出生之后,柴静的爸爸妈妈忙着工作,很少能抽出时间照顾小柴静。但身为教师的母亲并没有因此怠慢对小柴静的教育。但身为教师的母亲并没有因此怠慢对小柴静的教育。在柴静两岁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教她识字。母亲用纸板剪成四四方方的卡片,在正面写上“日”、“月”、“水”等字,背上写上这些字的汉语拼音。母亲把做好的认字卡片用绳子穿起来,做成一串特别的项链,套在小柴静的脖子上,让小柴静拨弄着卡片,提高学习认字的兴趣。当别的孩子还在呀呀学语的时候,聪明的小柴静在母亲的培育下,已经认识了很多字。
由于识字比较早,柴静4岁就进入小学了,为了照顾小柴静的生活和学习,母亲把柴静带到自己任课的班级,让她坐在最前排,和其他7、8岁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虽然母亲也知道柴静可能听不太懂,但仍让她坚持听课,每天放学回家还背诵和默写课文,即使柴静对很多课文似懂非懂,她还是会兴致勃勃的阅读它们。再稍大一点,母亲就开始为柴静订阅各种儿童报刊。并在家里腾出一间小屋子为她当作书房。每天放学回家后,小柴静都会自己拿着小板凳坐在小书房里看小人书《岳飞传》。柴静对文字的敏感与生俱来,小小的年纪,对所有写字的东西都十分感兴趣,无论是父亲订阅的《中医杂志》还是母亲的函授书籍,她都能读的津津有味。
在柴静上四年级的时候,妈妈调换工作,全家人都跟着她搬到她所执教的学校。小柴静的行李只有两件,一件是爸爸开完药后留下的漂亮小药盒,里面装几枚硬币。还有一件是一本《唐诗三百首》。带着这些东西,12岁的柴静由小学升上了中学。13岁时,柴静接触到了广播。她开始贪恋广播里的热闹人声和深入骨髓的歌。柴静从那时才知道,广播可以给人带来一个如此新奇的世界,那一刻,柴静梦想着能做一个电台的广播主持人,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离开这个地方,过上一种另外的生活方式,自己要“更自由,要过和身边的人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1991年,15岁的柴静到湖南长沙读大学,对广播的喜爱依然不减,最喜欢听音乐排行榜和谈心节目。后来她终于鼓起勇气,写信给湖南经济电台红极一时的主持人尚能表达自己做主播的想法,她说:“可否帮我成就梦想?”这句话促使了这位名主持马上给柴静打了电话,让她去面试。七月份的长沙,天气酷热,柴静借用学校广播站录节目,录完以后,汗水把衣服全都浸透了。面试通过以后,柴静开心极了,她开始做她的第一个节目——《另一种声音》。
第一次坐到真正的演播室里,柴静没有恐惧和紧张,她觉得自己就属于这个地方。此后,她每天都会带一沓稿子和磁带去做节目,整个暑假她没有回家,留在了长沙做节目。那段日子,她和家里失去了联系,常常翻箱倒柜地凑足5毛钱,跑到楼下买一袋最便宜的方便面,计划着吃一整天。长沙很大很热闹,但是无亲无故的她却倍感孤独,每天都在过着同样的生活:骑着自行车去做节目,然后再骑车回来。即便如此,她仍然觉得很快乐、很安心。
日子就这样在忙碌中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毕业的时间。柴静在学校学的是财会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山西太原铁路局工作。恰好长沙当时要成立一个新的文艺台,柴静去应聘,考核之后就留下了。她毅然辞掉在别人看来既稳定又舒适的工作,带着户口和工作关系到湖南文艺电台做节目,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简陋的租住房里,柴静从来不会感觉苦闷,因为心中有梦,她坚信,这些困苦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过眼云烟。
柴静白天忙工作,到了晚上,与她相伴的只有广播中的声音。她喜欢听新加坡电台林伟的《点一盏心灯》,他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灯火。”这句话让柴静感触很深,她决定做电台午夜节目。柴静就和电台的领导申请做一档午夜节目,甚至可以不要工资。随后,她创建了名为《夜色温柔》的晚间节目,一做就是三年。
那时的柴静只有19岁,年少的她心里只想着去实现心中的这个梦想,全然不顾自己身处异乡的孤独与寂寞。柴静说:“一个人为自己的工作神魂颠倒是多么幸福。”那个时候她主要是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什么事情都谈。其实那个时候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帮助别人排忧解难,毕竟她只有19岁,但是想用声音激发一个有想象力的世界,想用声音为更多的人赶走寂寞。她只需要说“我在,我听到了,我懂”这样的字眼,只要有一颗真诚的心就足够了。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柴静主持的这档《夜色温柔》变得十分红火,之后的几年,她基本都是在电台度过的。柴静在每个夜晚用真诚的声音陪伴着孤独的人们,她的声音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在节目里,柴静常常会接到从北京、香港、西藏等地慕名打来的电话,她去大学里做演讲的时候,时常都会有桌椅挤坏的场面出现。
柴静22岁的时候,顺利地当上综艺部副主任,成了湖南最著名的主持人之一。五月的长沙,茉莉花开,景色怡人。凌晨两三点男人们成箱成箱地喝着啤酒,女人们吃着东西。柴静经常能看到大街上享受着这种安逸生活的男人和女人们。她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种莫名的恐惧让她感到害怕。
柴静对现有成绩的不满足,使她几经考虑做了个令所有人惊讶的决定:辞职去北京读书。她不甘心让自己的生命就这样达到顶峰,她需要寻找可以不断超越的未来。她放弃了自己已经拥有的光环,到北京广播学院做了一名学生,睡在蓝白相间的格子床单上,学的是电视编辑,生活简单而有激情。
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不到半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她打电话过去时对方说已经招聘完了。“你们不是想要优秀的记者吗?这还有期限吗?”她的一句话,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对方让她第二天去试试。第二天她去应聘,负责招聘的人看看她说:“你长得挺漂亮的,不愁没出路,回去吧。”就这样,她被打发回来。没过多久,《三联生活周刊》给她打电话说他们要做一个封面周刊,问她做不做,柴静二话没说,立即答应下来。她用了三天的时间写出两万多字的稿子,就在她放假准备回家时,编辑打电话说让她把两万字改成两千字,她用了两个小时把稿子改完,跑到车站时离开车还有五分钟。之后,柴静在北广[微博]的日子一直在做《三联生活周刊》的兼职记者。
当柴静在《三联生活周刊》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湖南卫视邀请她做谈话节目《新青年》的主持人,当时《新青年》是湖南卫视改革后的一个新栏目。柴静答应了,于是她开始一边上学,一边在电视台做《新青年》的主持人。她在做节目的时候,采访了各行各业的名人,如,米丘、黄永玉、蔡琴、张朝阳、方兴东、吴士宏等。柴静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证明《新青年》是文化先锋,就做了一期关于20世纪 70年代新锐诗歌的话题,请来号称用上半身写作的女诗人和用下半身写作的男诗人做嘉宾,事后证明她的这次挑战成功了。柴静在节目中变得越来越成熟,她总是能将生命中的偶然与必然的交汇、世事的沧桑浮沉刻画得玲珑有致。
一个喜欢挑战人生未知极限的人是不会安于现状、按部就班地生活的。北广毕业后,柴静并不满足《新青年》中驾轻就熟的工作,于是进入了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时空连线》节目,做记者兼主持人。这对柴静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和挑战。在央视工作之前,柴静没有受过什么挫折,但是来央视做节目之后,一下就蒙了,不能指望别人手把手地教你,只能自己不断地摸索学习。
柴静在没有名校的学历背景、不是新闻专业出身的情况下,度过了一段痛苦的适应期。文静柔弱的柴静开始时被同事认为不适合做新闻记者,当时她的压力特别大。柴静为了做好节目,从蹲马步开始学起基本功,流汗流血、风吹日晒。她用最笨拙的办法,像蚂蚁一点一点地搬运食物一样,一步一步竭尽全力地去学习,自己做策划,观摩同行的节目,上机编节目,每天都待在演播室里,熬夜到凌晨三四点。
那时候柴静在采访前,一定是要求自己花很长时间准备做足功课的。有时候,采访完了夜里编片子编到三四点,然后送到台里。柴静是临时工,进不了大门,只能请导播到大门口来接带子。当时柴静住 18楼,回去太晚电梯停了,好不容易爬上去,编导打来一个电话说有问题就再爬下来。
柴静能从一个文艺青年成长为独立思考、探寻真相的新闻斗士,经历了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刚进中央电视台的第一年,柴静完全找不到做新闻的感觉,不知道如何提问,真正开始找到做新闻的感觉是在采访新疆地震时。
当时负责人白岩松对柴静说:“去喀什,给你半个小时去收拾一下东西。”凌晨,到了喀什,落脚在一片瓦砾、断壁残垣之中。人们正在举行葬礼,柴静根本来不及去思考什么是新闻,新闻就像一盆水兜头浇下来。倒塌校舍旁的两个小女孩,从废墟中走出来的老大爷,倒腾的半截房里湿漉漉的被子,让柴静活生生地感受到了什么是新闻,让柴静找到了做新闻忘我的感觉,找到了新闻中最鲜活的元素。
之后,柴静进入《新闻调查》,她更喜欢到现场去发现,深入一线进行采访。柴静觉得自己在《新闻调查》中找到了自我发展的理想平台。新闻记者不仅成了柴静的职业身份,也成了柴静的生活方式。

2003年,柴静参加了《北京“非典”狙击战》的拍摄,成为最早冒死深入非典第一线采访的记者之一。惊心动魄的现场气氛、摇晃的镜头、柴静身穿白色防护服的瘦弱身影和苍白的面容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熟悉柴静的朋友着实为她捏了一把汗,节目播出的当天晚上,柴静接到了数量前所未有的电话,感动之余,她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认识这么多人。但是一整晚柴静都没接到妈妈的电话。这让柴静心里感觉不安。直到播出的第二天晚上,柴静才主动打电话给妈妈。柴妈妈在电话那头说:“我昨天在邻居家看了节目了。”边说她边哭了——直到那个时候,她才知道柴静最近的几天里做了些什么。
但是柴妈妈并没有指责柴静,反倒帮她出起主意,她建议柴静采访在国际上享有声望的流行病学权威何大一教授,还建议她做关于流行病传染链的调查。后来,当柴静要去艾滋病孤儿村采访前,她给母亲打了电话,母亲在电话那头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说:“去吧,妈妈支持你。”
柴静说,如果母亲狭隘一点,给她一些阻挠,她可能在做类似这样有危险的选题时,就不会太投入。现在,柴静会就她面对的一切都跟母亲沟通,比如何处理和领导、下属的关系,如何应对工作中的突发事件。母亲往往会以一个过来人身份,给她许多建议。
“非典”之后,柴静离开演播室,从主持人成为了一名调查记者。她坚信:“除非亲身抵达,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努力发掘,否则就不可能认识事实真相。”“做新闻要有笨拙的精神,不要不假思索,”她说要对评论有警惕,要对真相有洁癖。”
正是这种执著追寻真相、独立思考的精神使柴静对新闻调查有着独特的见解:真正的调查报道就是探寻未知的过程,是不断遇到障碍、克服障碍的过程。没有未知就没有调查。调查是以已知为起点的,不需要还原已知,而是探寻未知是什么。最精彩的地方往往就在你没有设计到的细节中。
对柴静来说做记者不仅是她的职业身份,也是自己生存的一种方式,因为调查真相就成为她的天职。柴静着迷于这个真实的世界,愿意静下心来沉浸其中,去领略那些撼动人心的地方,去体会黑暗深处的光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柴静的主持风格日渐成熟,她不再是那个在最初会炫技的主持人——“你看,我的问题多漂亮,我把对方问倒了,我赢了。”柴静深知这对于解决问题毫无帮助。现在的她经过不断的思考,明白了自己节目的重心。不轻易做出褒贬,要做的是细节的探究和幕后真相的挖掘,能让对方自由地表达,帮助公众得到尽可能多的真相。
真正了解到世界复杂性的柴静没有轻易责难和赞美的习惯,更多的是学会了宽容和体谅。今天的柴静是做新闻的楷模,这个昔日的文艺女青年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新闻斗士,永远独立地思考,永远与真相站在一起。
柴静坦言,三十年来她努力从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大的共同体中把自己剥离出来,离乡背井,就是为了找到自己。来京工作十多年的柴静至今仍然租住在一个一居室的小屋中,但她表示自己对此从来不在意,“生命不是一张属于你的床铺,生命有时就在一瞬之间”。
当有人向柴静提问:“柴静,你幸福吗?”聪明的柴静没有透露个人的感情生活,是用胡适的一句话来回答:“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即使开了一辆老掉牙的破车,只要在前行就好,偶尔吹点小风,这就是幸福。